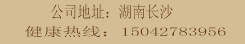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埃及 > 人口民族 > 在埃及卖内衣的中国人
当前位置: 埃及 > 人口民族 > 在埃及卖内衣的中国人

![]() 当前位置: 埃及 > 人口民族 > 在埃及卖内衣的中国人
当前位置: 埃及 > 人口民族 > 在埃及卖内衣的中国人
PeterHessler,又名何伟,《纽约客》记者,作家。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优秀作品,如《行路中国》、《甲骨文》、《江城》。他的妻子张彤禾也是一位作家,曾出版《打工女孩》。夫妻俩目前定居在埃及开罗。
艾斯尤特城(ThecityofAsyut)坐落在尼罗河呈月牙形弯曲地带的上埃及(UpperEgypt)的中心地区,尼罗河西岸有一所大学,一个火车站以及大约,的人口,另外还有三位中国移民开的内衣铺子。这些内衣店不难找,我第一次去艾斯尤特的时候打了一辆出租车,我问司机城里有没有中国人,司机二话不说,直接沿着尼罗河岸驶去,之后拐进一连串的小巷子,最后来到一块用阿拉伯语写着“中国内衣”牌子的店铺前。另外两间店铺,分别叫“中国之星”以及“Noma中国”也在距离这家店铺不到一个街区的地方。
这三家店铺都是浙江人开的,他们都卖些色彩艳丽,不咋实用的便宜玩意儿,例如长筒袜、只能盖住部分胸部的睡袍、以及用羽毛装饰着的丁字裤。还有一些透明的上衣上挂着叮铃咣啷的塑料金币,这些衣物的牌子也都是什么LaughGirl,ShadyTexLingerie,HotLoveItalyDesign,SexyFashionReticulationAlluring之类充满挑逗意味的短语。
上埃及区是整个国家最为保守的区域。几乎所有穆斯林妇女都戴着头巾穿着niqab(一种将全身包裹的严严实实只剩眼睛露在外面的黑色袍子)。很多城市几乎没有旅游业,更别提工业了。艾斯尤特是全埃及最为贫穷的省。除却少数叙利亚游民偶尔带来的集市以外,外国人在这里经商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我还是发现了来自中国的内衣商人分散在这片区域。在BeniSuef,一个名叫“叙利亚集市”的露天市场,两位中国内衣商贩见缝插针,和酷爱买卖便宜衣服和小装饰品的叙利亚人做起了生意;在Minya,往南部的一座毗邻的城市,它的购物中心里有一间名叫“中国内衣角”的铺子,入口处贴着可兰经里警示嫉妒的谚语。在更远一些的Mallawi,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妇在卖丁字裤和睡衣,而对面的Mallawi博物馆在他们到来之前刚刚被一群伊斯兰教的暴徒洗劫一空并付之一炬。
再往外延伸英尺,我总共发现了26位中国内衣商人:四位在Sohag,十二位在艾斯尤特,六位在Minya,还有俩在BeniSuef。他们好似一群捕猎的猫在划分彼此的势力范围:在尼罗河谷,每隔30到50英里你就会看见一群中国内衣店,具体的店铺规模会依据当地的人口可大可小。比如开罗拥有足够多的人口,因此大约12家中国内衣店铺在那里驻扎。董为平,一位在开罗拥有一家内衣制造厂的中国老板告诉我说他有四十多位亲戚在埃及,并且卖的都是他的厂出产的内衣。其他中国人卖的内衣都是埃及人自己生产的。对于中国商贩来说,这是他们通向埃及的窗口,他们靠卖内衣生存。
通常来说,他们白天比较晚开业,但是晚上会营业很久。他们无所谓过不过春节,自打Ramadan的日落伊始,他们就开始摆摊儿卖内衣。冬天的销量比夏天要好,母亲节好似就是专门为卖内衣而设的,但是任何时刻都比不上情人节,所以今年的情人节,我告别了我的太太,一个人驱车四个小时来到艾斯尤特,专心观察来中国之星买内衣的顾客,直到深夜。
“中国之星”就在一所名叫Ibnal-Khattab清真寺旁边,不久就有一位酋长来到了店里,他高高胖胖的,有着深色的肤色,很强壮。他穿着一件亮蓝色的袍子,仔细地裹着穆斯林头巾,他身后还跟着两位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女人。酋长在门口站住了,那两个女人在一排排内衣堆里认真搜寻着。不一会儿,其中一个女人举起一样东西,酋长则摆摆手表示自己的看法。
情人节是“中国之星”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接待男顾客最多的时候。通常来说,来购物的大多是女人,她们会买些休闲性质的睡衣。没有任何上埃及地区的妇女会在公共场合穿着这类衣服,但在家里穿还是可以的。所以说么,埃及的女人需要两套衣橱:一套室外一套室内,这就是服饰市场获利颇丰的原因之一。通常她们也会发展第三类服饰选择,那就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性感的衣服。这两个穿着niqab的女人迅速找到了两件族长认可的衣服:配对的丁字裤和胸衣,透明的睡袍,一红一蓝。
酋长开始和陈亚英讨价还价,她和丈夫刘军一起经营这家店铺。在埃及,他们称呼自己为Kiki和John,俩人都身材矮小,Kiki刚好抵到族长的胸部高度。她今年24岁,看上去好像刚刚过了书呆子气的青少年时期,她带着方形的眼镜,扎着松塌塌的马尾。她一边操着浓重的口音对族长说着阿拉伯语“thisisChinese!”一边拿着女人挑好的东西。她把价格降到埃及镑,差不多20美金的样子,但是酋长讨价说就好啦。
我不清楚这位酋长跟这两个女人的关系。当我们攀谈的时候,酋长说他为宗教捐赠部工作,专门负责监督的清真寺的各项事物。大多数虔诚的穆斯林教徒认为不应该庆祝情人节,但当我提到情人节的时候他并没有恼火。我实在找不出更好的方法谈及这两个女人,在上埃及区,直接了当地询问男子关于他们的妻子是不合适的,尤其当她们穿着niqab的时候。无论我何时问起男人对自己妻子穿niqab的看法,他们的回答都如出一辙:这是为了防止别的男人觊觎自己的老婆。但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这恰恰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女人裹的越紧,我就越想要知道这层层包裹的布料后面有着怎样的表情,我开始任由思绪乱飞:这两个女人都是他的老婆吗?她们是不是会一个穿着红色,另一个穿着蓝色的内衣陪他过情人节呢?
酋长和Kiki还在为最后的10埃及镑争论着,此时第二位顾客出现了。“我得走了”,酋长说着递给Kiki一些钱,“我是个酋长,我必须付钱!”但是Kiki立马把钱扇到了他的胳膊上,坚定地喊着“不够!还要10镑!”酋长的眼睛瞪的大大的,然后,炫耀般的面对麦加的方向,闭上了双眼,做出开始祈祷的姿势。他站在内衣店中间开始念念有词:(我译)咪咪妈咪轰...
“好了好了拿去吧!”Kiki说道,转身立马去招呼另一位顾客。酋长乐呵呵的离开了,后面依然跟着那两个女人。Kiki后来告诉我说她觉得其中一个女人应该是那酋长的母亲。在我看来,这么一假设完全改变了故事的叙述风格啊!但是丝毫没有减少它的趣味!Kiki没有其他可说的,对于她来说交易结束的那一刻故事就结束了。
中国商人很少琢磨他们的埃及顾客,甚至包括那些老客户。Kiki告诉我说有些当地的妇女一个月会来两三趟,有时她们会购买一百多套睡衣和内裤,所以“中国之星”每两个月就要进一次货。当我让这些中国商人分析个中的原因时,他们经常会说这是因为对公共服饰的严苛要求,所以埃及人喜欢做爱。“如果你一直没机会让自己看起来很美,精神上会比较难受吧。”陈环太,另外一个在艾斯尤特的中国内衣经销商说。“我们都知道她们在外面的时候要穿那么多衣服,裹那么紧,当然希望在家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的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咯。”
但是这个主题仍然不会引起中国商人很多的兴趣。他们大多数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并且不认为自己在埃及会有什么文化上的交流。至于宗教,他们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似乎没有任何偏见或者预先接受的观点,他们会依据个人的直接经验评判所有的信仰。“那些戴十字架的是穆斯林吗?”一个中国商人问我。他在Minya已经居住了近四年,一个充斥着部落纷争的城市,甚至一些基督教的教堂都被暴徒用石油炸弹毁坏了。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意识到他依旧认为戴头巾的妇女和穿niqab的妇女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也符合逻辑:他注意到了这些女人举止有差异,所以他们可能信仰不同的东西,伊斯兰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总体说来,相比于基督教徒,中国商人更喜欢埃及的穆斯林顾客。部分原因可能是穆斯林教徒是更忠实的内衣顾客,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容易讨价还价。科普特人是一个更为富裕的少数民族,而这也正是中国商人唯一所关心的--对于他们来说,宗教本质上不过是商业的另一种特征罢了。
开始时,我对于中国内衣商人在对当地文化如此不“感冒”的前提下还能成功经营很纳闷。在极度贫困的Mallawi,一位名叫叶达的中国商人邀请我去他破旧的公寓吃午饭,然后我们发现他无意中买了骆驼肉。他和他的妻子在年八月经历了上埃及区那场极度糟糕的政治动乱之后搬到了Mallawi。夫妻俩的家里只有一本名叫《你是你自己最好的医生》的书。他们几乎不说阿拉伯语或者英语,他们也没有任何中文-阿拉伯语对译的字典或者语言教材,实际上他们也从来没有遇见过任何拥有这些工具书的中国商人。和中文不同的是,阿拉伯语会根据性别的不同有不一样的变体。而这些中国商人正是通过聆听和阿拉伯妇女的交流而慢慢习得一些固有的词语结构和语法规则。我觉得这些可以看作是一种内衣方言吧。
在内衣方言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短语叫“我有大一码的”。中国商人经常用这个。埃及人通常块头比较大,他们非常幽默并具有领袖气质,例如那天在“中国之星”看到的那位酋长。相反的,小个儿并严肃的中国人可以找到办法从话题的中心隐去。这种差异看起来正好符合内衣交易的气氛。中国商人身材矮小,知道的也不多,在意的则更少,所有的这些品质让埃及的顾客十分的放松和惬意。
这些内衣店经常会雇佣一些当地的年轻埃及女孩做助手,而这些埃及女孩则很少跟自己的老板交流。但是她们通常对自己的中国老板十分忠心耿耿。在上埃及区,女人去工作本身就很少见,而工作的那些女孩似乎也更热衷于参加各种反抗类的活动。在“中国之星”,Kiki和John雇了一位18岁的名叫RahmaMedhat的埃及女孩。Rahma也裹着头巾,但是两双手上都有骷髅图案的刺青。她说这是在一个科普特人的教堂弄的。在埃及,基督教徒通常会把十字架图案纹在右手或者右手手腕上,而教堂是城里唯一拥有纹身工具的地方。而对穆斯林教徒来说,纹身似乎是一项极为野蛮的活动。
Rahma得意地告诉我说当她父母看到她纹身时简直气急败坏,他们更反对她去内衣店工作。在她受聘之前的那个女孩也是因为家庭问题离开的。John告诉我说他一直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看到之前那个女孩的脸上和胳膊上有淤青,有一天她父亲来了并在店铺门前的街道上狠狠地揍了那女孩一顿。
尽管如此,多数的助手还是因为经济情况窘迫而来工作。在Minya的中国内衣角,一位名叫Rasha的27岁女人告诉我说她十年前就开始工作了,当时她母亲去世了,父亲因为一场车祸成了跛子。Rasha还有四个妹妹,她挣的钱已经帮助其中三位妹妹都结了婚。在过去,她曾经为另一家中国内衣店工作,她告诉我说她永远也不会为埃及人打工。在她看来,中国人很直接很诚实,她很欣慰她的中国老板都选择远离当地的舆论网络。“他们很会保密的”她告诉我。
Rasha告诉我说当地埃及人没办法像中国人一样高效地卖内衣。“我没办法描述他们(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她说,“但是他们就是可以看着这些东西然后卖给女顾客,就这样。”一个埃及人可能会一边看看他卖的这些东西,然后看看女顾客,他可能会开个玩笑或者攀谈一下啥的,Rasha谈到她之前的那位中国雇主无不敬佩的说:“他卖东西的时候非常专心,当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卖主的想法,中国人的脑袋里从来不会意淫女人的身体。”
内衣方言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词叫arusa,也就是“新娘”的意思。中国人通常会发音成alusa,而且他们乐此不疲地使用着这个带着口音的词语。在开罗的邻里街巷,中国人会背着一篓子裙子和内衣挨家挨户的叫卖“alusa!alusa!”在中国人的店铺里,他们用这个词来吸引潜在的客户,对于当地人来说,它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有趣的恭维,“美丽的新娘子!来看呀!blide!你想要什么呀,新娘子?”
在情人节这天,在那位酋长离开后不久,一位真正的新娘子来到了“中国之星”。她今年19岁,婚礼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举行。新娘是和自己16岁的未婚夫一起来的,同行的还有她的母亲和弟弟。Kiki开始从架子上为她挑选合适的衣服。“新娘子,你喜欢这个吗?”她拿出一个写着“NetLadystockingSpringButterfly”的盒子问到。新娘子开始研究那些长筒袜,然后她递给了自己的未婚夫,然后未婚夫递给了她的母亲,最后母亲递给了她的弟弟。盒子前后分别印着一张照片,一个穿着高跟鞋的斯拉夫女模特站在一个书架旁边,她穿着从脖子到脚踝的蕾丝紧身衣,一条丁字裤、外带一副空洞的表情(我实在难以想象这个招贴画。。。)。新娘的弟弟看了好久。最后长筒袜被放到了一堆其他被选购的东西里面。
在埃及人的婚礼当中,新郎是该负责购买公寓和家具的,新娘负责购置一些小物件,厨房用品或者衣服,包括内衣。自年以来,埃及和中国的贸易合约让更多的衣服或者内衣更顺利的进入埃及市场,中国的内衣店铺仿佛一夜之间在埃及满地开花。董为平,开罗最大的内衣供销商,告诉我说,除了他的工厂生产的内衣之外,他每年还需要从中国进口10集装箱的女士内衣。在“中国之星”,这位新娘和她的家人花了一个多小时选购了25件睡袍-内裤套装,10套内衣内裤,10件胸罩,以及一条长筒袜。
这位新娘的母亲总计花了相当于美金的埃及磅,而且她还告诉我说婚礼前,她们还要再买两三次。交易当中,当Kiki拿出一件睡袍时,这个购物小团体爆发出了由衷的赞美。“你觉得如何?”Kiki举着这件透明的外加粉色丁字裤的睡袍询问着顾客的意见,未婚夫惊叹道:“我的老天!这太美了!”他目前是艾斯尤特的一位律师,而新娘则在大学念法律。新娘谈吐得体,长的也很漂亮,尽管她当时穿着一件没有任何形状的牛仔裤和一件厚重的绿色外套,并且紧紧地裹着保守样式的头巾。
这一家人深深地震撼了我,他们看上去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传统家庭,关于这次的购物他们当中任何一个都没有感觉难为情。如果实在要找出什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全程弥漫的这种毫不扭捏的欢乐氛围,新娘也完全没有一点点的尴尬。我很确定即使是最自信的美国妇女也会被和未婚夫、母亲、弟弟一起买内衣这种想法而吓到,更别说是在两位中国商人、他们的助手以及一位外国记者在场的情况下了。但是我曾在上埃及区的其他店铺也目睹了相似的场景:一位新娘被全家人以及朋友所簇拥着来买内衣。在人们的脑海里,这种“仪式”很大程度上都和性是完全不挂钩的。
对于新娘需要观众的这种状态,中国商人有时跟我解释说埃及的女人买这些东西是为了在晚上给自己的丈夫跳舞。他们的这种理论我猜测恐怕是受到电影里那些肚皮舞的画面影响,但是在寓意上来说没准是真的。每当我看到一位新娘和自己的家人一起选购内衣的时候,我总有种感觉这些女人是在为自己未来的角色做准备。在“中国之星”,我问了那位母亲她的女儿结婚后是否会成为一名律师,她说“当然不会了!她得待在家里啊!”她骄傲地说道,这份骄傲我从那些男人谈到整天待在家里的老婆时也感受到了。在埃及阿拉伯语里,新娘的另一个意思是“洋娃娃”,孩子们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他们用来穿或者脱衣服的玩具。
在艾斯尤特,Kiki的父母林羡非和陈彩梅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中国人社团。林在浙江的一个半亩大的农庄里长大,因为贫穷,他在五年级时便辍学了。在90年代,他靠在北京做服装贸易发了点小财,之后在年,他听说家乡的一些人去埃及打工赚钱去了。他研究了一下地图决定来艾斯尤特定居因为他觉得这里是埃及最大最有名的城市。(实际上,Luxor更大)
“我知道我会是这里唯一的中国人,所以机会会更多一些。”林告诉我说。在艾斯尤特,他建了一个类似露天市场的棚子。开始时他只卖他从中国带来的三样东西:珍珠、领带和内衣。在来之前他根本不在乎埃及人是否想要这些东西,关键因素是尺寸。“他们很容易塞进行李箱”他解释到。
林很快意识到艾斯尤特的人不是很喜欢珍珠,他们也不会用到领带,但是他们喜欢女士内衣,所以他开始细化他所卖的商品,而他的太太也从中国飞来埃及帮他。在开罗和上埃及区,中国的内衣制造和进口业迅速开始扩张,最终林和陈在艾斯尤特租了一个店面。他们邀请自己的亲戚和朋友过来在城里开了另外两家店铺。当林和陈专心建造他们的内衣王国时,他们也注意到在艾斯尤特有很多的垃圾被堆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个现象的人,但是他们是第一个回应的人,之后他们从中国进口一种原产于江苏的聚乙烯-对苯二酸盐洗洁生产线,企业通常用它来压碎塑料瓶,洗洁并在高温下烘干重新打磨,最后当做回收材料贩卖。
“我开始看到这些垃圾被到处乱扔,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回收它们并且赚钱”林告诉我说。他和他的妻子对工业一无所知,但是在年他们在上埃及区建成了第一个塑料瓶回收设备线。他们的工厂位于艾斯尤特西边沙漠的小型工业园里,目前有30个工人每天碾碎大概4吨重的塑料制品。林和陈将处理过的材料再卖给开罗的中国人,然后这些人又用买来的材料制成衣料,这些衣料然后再被卖到埃及的经销商们,也包括一些中国商人手里。一个塑料瓶子就这样在经过三重中国程序之后重新以内衣的形式回到了中国商贩的手里,由他们出售。
林告诉我工厂每年大概盈利50,到,美金,他的成功事迹启发了另一位埃及商人,他于今年早些时候也开展了相似的业务。尽管林和陈的事业一直蒸蒸日上,他们仍然住在工厂楼上的狭小公寓里,全天都身处机器的轰鸣之中。林今年五十岁出头,看起来却像老了十多岁,他目光充满疲惫,由于长期不恰当的饮食,他还患有严重的胃病。他很少谈及当地的文化,但是有一次当我问他埃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的时候,他那强有说服力的回答震惊了我。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平等。”他立即说到。“在这里女人只能呆在家睡觉,如果她们想发展自己,第一件需要解决的事情就是这个。这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所做的事情。这里的人才被浪费掉了。看看我的家庭,你也看到了我太太是怎样工作的,如果没有她,我们也不会达到今天的成就。再看我的女儿,她也在经营着自己的店铺。如果她们是在埃及,她们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些。”
几个月之后,当我再度拜访艾斯尤特,因为老林需要回国看医生,所以他的太太陈一个人在管理整个工厂。一天下午,我在工厂门前站着时,两个邻近村庄的年轻人载着一车的塑料瓶子来了。其中一个叫Omar,他告诉我说自从知道有中国人开了这个厂,他五年前也就是12岁的时候就开始这项营生了,现在他和一辆卡车司机合伙运送这些瓶子,他们会和当地的小孩子讲好条件让他们帮忙去街上捡瓶子。Omar说他通常一天能赚至少埃及磅,差不多13美金,而这是当地劳动报酬的两倍。正当我们谈话的时候,陈突然从门口出现,她戴着一个绣着“我的玩伴”字样的花围裙,面带愠怒吼道:“你们为什么带水过来?” 她将一些一公升的瓶子掷在Omar和他同伴脸上,“你们太坏了!”她用支离破碎的阿拉伯语继续吼道,“你们简直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我很生气!生气!这不干净!!不干净!!!”
陈更是在一些空瓶子的下面发现了装满水的瓶子,原来这些回收者想要玩些小把戏来压压秤好多拿点钱。她继续不停地吼叫:“你们是阿里巴巴!!!”最后我终于明白她是指“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我从没在埃及听到任何人如此地使用“阿里巴巴”,但在此刻这是陈无限循环的一种发泄怨怒的方言,Omar躲的远远的直到她回到门内。
“我的老天!我真希望她出门被车撞死!”Omar说,“她曾经用砖头砸过我们。”
一个工厂的守门人名叫MohammedAbdulRahim却说Omar活该被砸。
“又不是我干的!!”Omar嚎叫,“那些屁孩子干的!是那些捡瓶子的屁孩们干的!”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Mohammed告诉我说。他解释说因为袋子里总是有东西藏在里面,而陈和林总能发现。过了一会儿,陈再次出现,继续开启她另一轮的“阿里巴巴”攻击模式,最后她终于冷静下来,坐下和Omar讨论一千克瓶子的价格。整个卡车装了磅瓶子,差不多是多美金。当Omar的合作伙伴坚持说应该再加1埃及磅时,陈像甩麻将牌那样把手中的硬币狠狠拍在桌上。
“穆斯林钱!”陈喊到,这次她换了种吼法。两个小伙子刚走,她的怒气就消了。在工厂里,她貌似培养了一种埃及戏剧性的品质。她将头发盘在脑后,有着农民般宽阔、饱经风霜的脸和一种灵活的谦逊。有一次,当我夸奖她居然有勇气来艾斯尤特这种地方定居时,她轻轻扫一笑,淡然地说:“我只是比较无知罢了,我文盲一个,我只能写我的名字,但是写的很难看,我从来没上过学,一天也没有。”
每到周五,林和陈都会开车去艾斯尤特去看望女儿女婿以及两岁的孙女。有一次我在城里,小孙女的眼睛长了脓疮,John请我和医院帮忙做翻译。医生诊断说是感染了,并且怀疑是因为环境不洁净造成的。John说这是他女儿自打出生第一次看医生。这一大家子里面好像没人害怕在艾斯尤特的生活,他们也不认为自己算是成功人士。林和陈总是说自己的厂子其实很低级,可是每当我去看望他们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在想:这里是埃及,一个居住了8,,人口的国家,一个过去十年间被无数来自西方的工作者和数以亿计的救援物资倾注的国家,第一个南方的塑料回收中心是一座雇佣了30个工人、通过减少垃圾来补偿其他人并获得很多利益的工厂。所以为什么会是两个卖内衣的、并且一个是文盲另外一个是只有五年级文化水平的中国移民做到了呢?
我从未在埃及遇到过对改变这个国家感兴趣的中国人。他们经常会谈论他们眼中埃及的弱点-人民缺少工作伦理道德,缺少系统的政府领导,但是他们的语气明显不同于西方人。他们缺少西方人的那种沮丧感,中国人好似更能接受事情就是这样的一种局面。同样,中国人也没有罪恶感,因为中国没有在此殖民的历史,而且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和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都有交流和接触。中国企业家经常夸奖埃及人的友好以及他们乐于助人的天性,这两种品质在中国人看来恰好是中国社会最为稀缺的。他们也从来不对埃及革命抱有任何失望的态度,这不是因为他们相信“阿拉伯春天”(ArabicSpring)开始慢慢变好,而是因为他们首先就对所谓的阿拉伯王国没有任何的信仰。
年,当MohamedMorsi在改革后当选为埃及总统,他的第一次出访便选择了中国。第二年,他被军队除名,他的继任者AbdelFattahel-Sisi也很快地访问了中国。但中国政府对于埃及如此火速的易主事件并没有显示出多大的震惊。在开罗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位来自亚洲另一个国家的外交官谈论我和中国内衣商人的经历,她说他们的行为和远见让她想起了她心中所谓的外交。“中国人会给我们卖任何我们喜欢的东西,他们从不会发问,他们也不关心你买了东西之后拿来干嘛,他们不问埃及是否会进行选举,或者镇压人民,又或者把记者都投进监狱,他们不关心也无所谓。而美国人会想,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他们就不太可能会攻击我了,中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不会迫使这个世界都像他们一样。他们的策略是链接贸易,发展经济,而一旦你企图破坏这种联系,结果只会害人害己。”
过去的20年里,中国已经在非洲创造了许多诸如此类的纽带和联系。年,HowardFrench指出相比于美国,中国人和非洲的贸易整整多了两倍。French观察发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中国人实质上正在介入原有的老式殖民体系当中,过度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这自然地引起了当地人的憎恨。但是埃及不同,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中国人想要的自然资源。去年,埃及人出口到中国的总量是中国出口到埃及的1/10,这种贸易落差仍在扩大。其实中国在埃及的直接投资很少,他们在埃及投资排名的国家里面位居第20位。而在埃及的中国人大概有10,多。然而,埃及在整个中东地区却扮演者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角色,中东一半的石油是提供给了中国,而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货物都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的。另外,埃及的大学拥有来自中国大约2,名的留学生,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穆斯林。中国政府担心这些学生会受到穆斯林激进思潮的影响,而这也是中国当权者认为会危及埃及国内繁荣稳定的不利因子。
另外,中国在埃及的治国方略除去经济实用主义之外还需要一些更加政策化以及原则性的东西。中国目前正在加倍扩张其在开罗的大使馆。中国政要们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失势会为他们自己提供有利的机会。但是确定价值和目标这一过程似乎并不是中国政府的拿手好戏。“说实话,我认为即使在中国国内,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思想体系。”那位亚洲外交官告诉我。“即使中国人知道他们要倡导何种思想形态,他们也缺少类似韩国或者日本的软权力工具,这种工具便是类似于西方社会那种对发展型事业的大力投入(笔者认为这里她指的是政府对科学研究的大力资助)”在开罗,中国人建立了孔子学院意图弘扬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但是规模很受限制,并且埃及的宗教领袖也很排斥他们的这种努力。
没有一个确定的方针策略,中国转而求助邓小平时期的那种本能:有任何怀疑的话,那就建工厂。在沙漠里有个地方叫AinSokhna,离红海和苏伊士运河交界处不远。一个名为TEDA(天津泰达)的中国国有公司建造了一个名为中国-埃及苏伊士经济贸易的合作区。他们的座右铭是“合作让世界更美好”,在这个区域里的6平方千米的沙漠已经被开采为方方正正的宽阔街道。在它周围都是荒芜地带,最近的城市是苏伊士,车程距离一个小时。这个区域里有天津路,重庆路,以及上海路。工人宿舍也建好了,还有专门用来摆放运输容器的院子,这些容器外面都涂着鲜艳的颜色,几英里外的沙漠都能看见,就像太阳下即将被融化的lego堆一样。这里有一家中国餐馆,一个中国超市,以及中国理发店。中国人似乎对头发很挑剔,无论在红海附近的什么地方,只要有中国工人,理发店是肯定少不了的。
TEDA区域看起来就像是中国某个小城被连根拔起安放在了这片沙漠之中。类似的移植现象在全世界都屡见不鲜了。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计划在50个国家建造大约个经济发展区。中国想鼓励国内的企业走向世界,同时可以缓解国内对于自然资源的大量损耗。TEDA区域提供一定的补助和设备给企业们,50多个公司已经承租,大部分来自中国,他们通常规模比较小,还有一些是之前的内衣生产商。但是几乎所有的中国老板都跟我抱怨了同一个问题:他们招不到工人,尤其是好的女性员工。
“我就是招不到人啊!”许新,一位手机工厂的老板直白地告诉我说。在中国的摩托罗拉工作许多年后,许新想要来埃及寻求制造便宜手机的机会并出售给当地人。“这项工作需要很强的纪律性,一部手机有上百个零件,如果你出了一点差错,那整个手机就不会工作。埃及人太没耐心,他们老喜欢走来走去,他们没法专心工作。”他一直想招一些女性员工,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只能招些未婚的,这样的话员工流通就会比较频繁,因为大多数的人一旦订婚或者结婚就会辞职不干了,更糟的是,许发现年轻的埃及女人没法住在宿舍里,因为她们认为晚上远离父母是不对的,女性职员必须用公共汽车每天运送,这样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超过了三个小时。这直接导致许减少多个组装线的运行,一年后,他直接关闭了工厂。
其他人也有着相同的困扰。我遇见了王伟强,一个曾在中国东部靠制造白色ghotra头巾获利颇丰的商人。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王决定在埃及开展业务。“在这里我有非常好的埃及棉花,我的机器是最先进的,我大概投资了多万去建厂,但是这两年我损失了很多。而这全都是因为劳动力的问题,也就是工人的心态问题。我们的工厂需要每天24小时运行,而且不只有一个换班。为了达到这个要求,我必须雇佣埃及的男人,但是他们实在太懒了。现在我基本上会拒掉90%的男性应聘者,我只用女孩或者女人。她们都是很好的员工,但是问题是她们只能白天工作。”他想尽办法以延长白日的工作时间“我快疯掉了!”他说。
20多年前,当中国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老板们喜欢雇佣年轻的女工因为她们可以接受更少的薪水并且相比于男人更好控制。但是在一个传统意义上鄙视女性的社会里,她们反倒更加被激励,从而赢得了更多的角色和声望,社会关于女人的看法因此慢慢转变。如今在上流社会还是有很大的性别差距,女人极少数会赢得公司董事或者政府机要的位置,但是在工薪阶层,女性则拥有更多的经济优势,现在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听到人说想要女孩甚于男孩的可能性大多了。
埃及也有着类似的差别来激励女性去更努力的工作,但是传统却在阻挠着她们。在年的冬天,TEDA宣布他们即将加倍扩张园区的大小,但是我很难想象他们将要如何来填补劳动力不足的现实。同时,这个地区依然没有生机,尤其在晚上更是死气沉沉,没有晚间车床的声音,也没有年轻工人欢笑的声音。沿着工业园区的边缘,沙子吹进空荡荡的街道,我数了有个路灯是坏的。从古到今,埃及的沙漠里都充满了类似的庞大却又被误导的工程项目,TEDA却是最奇怪的一个。它是撒哈拉沙漠里被人遗忘的中国工业园。
在AinSokhna,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老板名叫吴志成,他将便宜的塑料碗碟引进了埃及市场。他雇佣了大概20个女工在他的组装线上工作,尽管员工流通很频繁-通常工人会待几个月然后就订婚或者结婚去了。过去在中国,他招募的那些女工都是差不多抱着一个离开家乡的模糊概念来到他的厂里打工,在迈出了第一步之后,她们进入工厂的新社区和宿舍,随之而来的便是愈加成熟的理想:寻求经济独立和成功。但是吴说埃及妇女工作的出发点就不一样,在这里,她们只是为了钱。
在吴的一部分工厂里,埃及工人存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买内衣或者将来缔结一段传统的婚姻。“我今年应该结婚了”SoadAddelHmaid,一个在组装线上工作的24岁女工告诉我。“但是好像又不可能,因为我还没能给自己买东西。”她说一段婚姻可能被推迟或者解除的原因就是有人没法给自己买想要的东西,她计划结婚后就辞职,而这几乎是厂里所有女工的想法,除了两个人。
而说NO的这两个呢也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违背传统价值的人。一个是年约50岁的FatmaMahmoud,她也是厂里唯一的一个已婚女性。她告诉我她早就考虑要离婚了,但是她的丈夫威胁她说如果离婚就不再给她任何经济支持。2年起,埃及妇女有权利终止婚姻,但是Fatma最终决定不这么做。“我的兄弟姐妹们告诉我不要这么做,因为在我们的传统里面离婚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我们是从上埃及区来,思维很封闭。”只有一个工友坚持认为Fatma婚后应该继续工作,这是一个叫Esma的年轻女人。先前她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是在离家比较近的苏伊士工厂里做库存,她的未婚夫也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但是后来他们分手了,Esma的父亲迫使她辞职因为和自己的前任在一个地方工作是不合适的。“作为埃及人,当你的父母给你下了指令,你必须服从。”所以现在她每天工作四个小时给人开公车,而这是一项报酬相比于之前更少,潜在机会也更少的工作。
吴关于埃及女性员工的结论很简单:只要她们缺少基本的逃离熟悉的本能,她们基本上就不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也以同样的看法评价埃及。“如果他们没有驱逐穆巴拉克,也许情况会更好点。”我经常听到中国企业家有类似的评价,在西方人看来这也许很愤世嫉俗,因为任何局外人都是希望埃及进行改革的。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观点也许更明朗,因为他们不戴任何有色眼镜地看待埃及,并且没有抱着他们预想的方式去改变埃及。在年的改革期间,西方人看到的是埃及强有力的社会变革,而中国人则认为埃及陷入了更糟糕的泥潭。对于中国企业者来说,他们所接触的只是地区性以及实用主义的层面,所以对于全国性的宗教以及政治改革他们并不在意。他们很少谈论政治或者穆斯林兄弟情谊之类的东西,但是关于妇女的地位问题却是屡屡被提及,因为这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他们在埃及的所有活动。一些中国人,例如内衣商人可以通过妇女获得利益,而另外一些中国人则挣扎在找不到足够多的女性员工的困扰里。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埃及的问题不在政治,不在宗教,也不在军队,而是在家庭!丈夫、妻子、父母、孩子等等。中国人认为在埃及如果这些关系如果不改变,那么就没有任何谈论改革的意义。
去年年末,中国人突然决定在工业园区建造四座游乐园。在国际钻井材料生产公司的对面,TEDA正在建筑恐龙乐园。尽管史前的主题已经延伸到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领域例如海盗船、宇宙飞船、以及用青蛙装饰的空中飞人,它们还想主打大型的电动恐龙模型例如霸王龙和异龙。一些园内的中国企业家们怀疑这是因为国内的游乐园业有人在兜售一些产品。没有任何一位TEDA的官员愿意给我一个明确的官方答复,但是其中一位员工解释说这个做法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工人前来应聘。“这样的话,人们就会愿意来公园,当他们在这的时候他们可以多多了解这个区域,”他充满希望的说。
三月的最后一个周末,TEDA邀请了园区里的每一个人参加游乐园的试运行。那天很热,还刮着大风,空中飞扬的沙子让很多人都远远地躲开了建在员工宿舍旁边的水上世界。另外两个公园一个叫“糖果世界”,另一个名曰“汽车世界”。大家好像都来了:生产塑料碗碟的吴志成,制造头巾的王伟强,还有以前卖内衣现在做衣料的张冰华。另外就是TEDA的高层官员,他们全都穿着黑色的西装,膝盖顶在狭小的玩具碰碰车的方向盘上,这里面许多干部都是从天津远道而来的,他们都抢着排队一遍又一遍地玩碰碰车。汽车世界的内部也被重新装潢了,丝毫看不出这里曾是一个因为缺少女性员工而倒闭了的手机制造厂。在街的对面,所有的电子恐龙都复活了,它们张开大嘴,通过一个个微小的扬声器一路咆哮,并杂乱地挥舞着四肢,仿佛它们发现自己被扔在了这片沙漠,全都惊呆崩溃了一样。
(文中所有人物姓名皆为直译,不保证正确性)
本文系笔者本人翻译,原作于年8月10号刊登在《纽约客》杂志上,所有版权属于PeterHessler先生及《纽约客》杂志社。
文/鳗鱼饭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简书平台,给作者写评论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mashaladicar.com/rdmz/5842.html